大运河与长江、黄河一样,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我与大运河的感情更加深厚,我的老家是卫运河畔的临西县,从小喝的是大运河水,看的是大运河景,走的是大运河桥,是大运河养育了我。
但真正知道大运河之伟大,还是上中学时读了刘绍荣写的《摆渡口》和《运河的浆声》之后,知道了它是世界上人工开凿最早、规模最大的运河,跨冀鲁平原,掠苏浙绿野,连海河、穿黄河、赴长江,再换钱塘江,全长3500余里,其长度是闻名世界的苏伊士运河的九倍,巴拿马运河的二十二倍。是中国古代南北交通的大动脉,更是劳动人民创造的一项宏伟的水利工程。河的南头是素有“人间天堂”之称的杭州,而北端就是直达皇城根下的拱卫京畿的重镇。
做为一名少小离家的游子,半个世纪以来,我去过不少运河沿岸的城市:北京、天津、杭州、镇江、扬州、聊城、德州、沧州,感觉运河就像一条金线串起的珍珠项链,熠熠闪光。古时候没有汽车、火车,更没有飞机火轮,只有马车牛车轱辘地驰过黄尘古道,运送大宗物品十分不易,而利用河流木船则省了不少力气。况且无论古代还是现在,水永远都是运量最大、运费最便宜的。尽管隋炀帝、乾隆皇帝等人利用运河下江南、游山玩水,但更重要的是保证了南北交通。尤其是元明清以来,它就像一条长长的脐带,一头连着富庶的鱼米之乡,一头连着雄浑的首善之区,营养中国大地和国家的统一。1292年,大运河实现全线贯通后,中国再也没有出现大分裂,大运河对于中国的大一统局面的形成功不可没,对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作用巨大。
京杭大运河,是与万里长城齐名的中国奇观,自吴王夫差伐齐凿邗沟起,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横贯于临西县的古运河段,全长39.2公里。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商末,距今已有千年。
临西域,夏属衮州,商末属纣畿内地,秦属巨鹿郡,两汉初属清渊县。后赵建平元年(330年)改名为临清县,治仓集镇东附近一带,金天会五年(1127年),因避水患徙治曹仁镇(今临清旧县)。1964年12月,国务院将临清县卫运河以西5个区划给邢台地区行署管辖,成立临西县。京杭大运河在临西县境内段称卫运河,在古代称隋唐大运河古道(又称永济渠、御河)和今卫运河两条线路。最让人不解的是,1970年临西新县城又选在古运河重镇古临清县原址相邻的童村,这听起来是一种历史的巧合,但也意味着大运河与临西县渊源流长。
隋唐大运河在临西县中部纵贯南北,从北端清河入境,向南流经黄夏庄、石佛寺、后堤口、龙旺、仓上、龙潭、尖冢等村庄,进入馆陶,其沿岸有鲧堤、古城遗址、龙潭寺遗址及尖冢码头遗址等重要的历史文化和美丽的传说故事,造就和蕴育了绚丽而壮观的故道运河文化。
元代,被尊为京杭大运河之父的郭守敬,通过对隋唐大运河截弯取直、弃弓走弦,京杭之间缩短路程800公里,奠定了今卫运河的走向和格局。留下河西的老街巷、八里圈清真寺、陈窑遗址、丁家码头险工等运河文化的遗址。
在我的印象中,大运河,不管它是隋唐时期,还是后来京杭时代,都是我家乡的母亲河,它虽然没有长江那样壮观,没有大海那样辽阔,但它都像母亲河一样,哺育一代一代我的乡亲,牵动着我的心弦,在我心中,它就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河。
大运河是中华民族的一张名片。从表面上看,它只是一条很普通的河流,但却给人以想象的空间。如果从地图粗略地看,长城跟运河所组成的图形,正好是个“人”字,长城是阳刚、雄壮的一撇,运河所代表的正是阴柔、深沉的一捺。不过,运河和长城不一样,长城现在已不能用了,仅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不到长城非好汉”啊!而大运河,则像一位阴柔温顺慈祥的母亲,仍继续默默奉献它的母爱,而不要求回报。千百年来,河道可以变迁,船只的结构也可以发生改变,可是运河上的船只来往如织,是一望就望到当年的。
临西人心目中,古运河在历史就像《清明上河图》一样,是浓缩了昔日繁华的卷轴。站在运河大桥上凝视这条运河,两岸的粉墙瓦黛鳞次栉比,码头石埠,错落有致,周边河浜纵横,幽曲深邃,勾画出一幅墙桅林立、万商云集的水运商埠画面。桥下一排排驳船推向水波,用力拍打着堤岸,很有底气的发出“哗哗”的声响,那沉闷的汽笛声,只有常住在运河边上的人们才会察觉到。也是明朝诗人李东阳所描绘的:十里人家两岸分,层楼高栋入青云。官船贾舶纷纷过,击鼓鸣锣处处闻。坼岸径流到此回,涛声日夜响春雷,城中烟火千家集,江上帆樯万斛来。
大运河最显著的功绩,就是漕运。漕运对于现代人来说是一个陌生的词。但在中国的王朝历史上,忙碌于京杭大运河之上的“漕运”,确是维持封建王朝统治的一根生命线。用现在的话来讲,它是朝廷利用水道调剂粮食,解往京师或其他指定地点的一种专业运输,目的是供宫廷消费、百官俸禄、军队粮饷支付和粮价调剂。据史料记载,1292年,大运河全线开通后,成为元朝及至大运河历史上最理想的纵向水上路线,仅从大运河北调南粮,就达到全国总粮食的六分之五。明朝时,因实行海禁,大运河就成为唯一的南粮北运水上通道,实际上成为明王朝的生命线。
漕运起源很早。秦始皇北征匈奴,曾自山东沿海一带运粮抵北河。汉建都长安,每年都将黄河流域所征粮食运到关中。元朝定都北京后,更加重视漕运,为此疏通水网河道。建立了漕运仓储。临西县尖冢镇正是因漕运而兴建的大运河的一个重要码头之一。在当地至今流传有:“一京(北京)、二津(天津)、三尖冢”的说法,这足以说明尖冢当年的繁荣及重要性。
尖冢地处大运河左堤北岸。因其“顺河迎流,单堤陡岸”地理优势,成为大运河最大的漕运码头。绵延三华里,堤外堡场占地200余亩。明清时期,满载木材、煤炭、粮食、棉花、瓷器、布匹、盐铁的船只往来如梭,络绎不绝。码头上每天存放着装卸的货船30多艘,每天吞吐量再百万公斤以上。每年都有百万石漕粮从这里运出。800多年来,一直是“漕运”与仓储的重地。其辐射面达周围200公里左右。当时,不但本地商人在此开有商号,而且济南、太原、天津、沧州等地的巨商大贾也在此开转运性质的商号,进行物流转运。村中的四条街上店铺林立、物资丰富。当时的尖冢,白日船来船往,商贾云集,买卖兴隆;夜间灯火通明,笙箫起舞、彻夜不眠。好一派繁荣景象。
时光流逝,今非昔比,随着近代海运、铁路得兴起,运河漕运的作用大大下降,有的地方出现断流现象。尖冢的河道自然也每况愈下,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青草浸满的河坝,只剩下两旁的绿化带,依稀显示当年的风采。
今临西县仓上村,时称仓集镇。是初唐时期,古临清县设置的官仓,据今已经有1300多年了。据考证,该村处于古县外中部偏西的位置,西依尖冢至仓上北引的古河道(方便运输),处于高阜处(能避水患),距县大堂较近,在祖野范围内(易于防护),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在官仓北部建筑区内,2米以下的地层中遗存丰富,有的地方砖、瓦堆竟达到2米左右,灶坑较多。遗址上收集到瓷片有唐代的黄釉、白釉碗、罐、执壶、灯罩等日用器皿,还有唐代早期的三彩陶器皿,更多的是宋代的磁州、耀州、建窑等窑口的日常生活器皿,并有有石弹遗存,为杂色石球状体,直径在3.5厘米左右,为弹弓专用。在那时,弹弓是一种远程性射杀武器,有着其他短武器不可替代的功能。大型的陶缸等消防储水应急之物,还有圆仓中心立柱,一个长约4米的柏木桩子,且立地牢固,卯榫规整,直径较大。隋代大运河开通之后,供大江南北的交通成为主流,人们不再为“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而感慨,唐、宋时期,大运河(永济渠)达到了极盛阶段。当时,官、民等南北交通多取于此。南来北往的商船,帆桅如林,南方的粮食、木材,北方的土特产品运量极大。尖冢码头的一般船只,在此要停留六七天的时间才能完成货物的装卸。繁华的商船、码头,给古临清带来了无限的商机。当时,临清是南方粮食的集结地,临清仓集镇的官仓成为北方地区最大的粮仓,是军用民需粮食的主要储备库和中转站。据传,宋代的包拯放粮还来过此地呢,故流传下周边村庄不论多远,均离临清十八里,因为那时以十八里为放粮半径。唐末五代50多年的战乱,各军阀也都以争夺临清仓为主要对象,从而引发了如“周德威临清保粮道”的许多次战争,一直持续到宋代统一之后方告结束。这说明,临清的官仓在五代时以成规模,此时的临西县永济渠(大运河)已成为重要运粮通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兵家的必争之地。
古人常将古临清与江南的苏杭媲美。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除去西京,就是仓上(古临清治所)。”这是大运河给临清带来的福音。
历史上,黄河屡在华北平原上肆无忌惮,摇手摇尾横冲直撞,给当地的百姓带来了种种灾难,民不聊生。历代统治者为保一方百姓平安,想方设法治理水患。在临西中部,有一条纵贯南北的古堤,相传为4000多年前鲧治水所筑,称为“鲧堤”。在山海经的神谱中,鲧是黄帝的孙子之一。在尧舜时代,他是朝中一位大臣。帝王派他到今临西一带治水,他组织黎民百姓在今山东冠县开始,经临西尖冢、东堤、龙潭、仓上、堤口、吕寨,过威县邵固,再至南宫县境修了一条宽二丈有奇,高二奇的堤坝,人称“鲧堤”。其雄姿感动了历代诗人墨客,对此多有吟咏。其中元代诗人萨都刺《过古黄河堤》云:“迢迢古黄河,隐隐若城势,古来黄河流,而今作耕地。都道变通津,沧海化为尘。堤长燕麦修,不见筑堤人。”如今“鲧堤”遗址尚存,高7米,宽15米,虽经千百年风雨侵蚀,还能显示出堤陡水湍的痕迹。
“鲧堤”受到后人敬仰,但最终让人佩服和怀念的是其子大禹治水三过家门不入的故事,代代相传,成为一种人人崇尚的美德。可真正变“水患”为“水力”的,是史上有名的杀父登基的隋炀帝杨广,他于大业四年(608年),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引沁水于河,北通涿郡(今北京西南),历史上称各济渠(大运河),宋代称御河,形成了以东都洛阳为中心,北通涿郡,南达杭州,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全长约1794公里的人工渠。它是世界上开凿最早、流程最长、规模最大的人工运河。
永济渠(大运河)是黄河北流的主要通道。不仅根除了其“水患”,而且给沿线经济社会注入了无限的生机和活力,造就一大批明珠城市,如今,山东临淄(淄博)山西上党(长治)等,最为显耀的是古临清县城(今临西县),它袤六华里,广三华里,总占地面积十八平方华里,城内南北大街纵穿,东西大路贯通,其交通“四通八达”,县衙、钟鼓楼、文庙、武庙、奶奶庙、县官仓、净城寺等楼阁星罗棋布,还有一些和家园林点缀其中,店铺林立,市井繁华、鳞次栉比、码头兴隆、车马喧嚣、人来车往,热闹非常,真个是“人间天堂”。
《水经注》云:“置临清余‘水东’,自石赵始。”“始是临清之各始于石赵,而县城则在‘水’。”据临西县杨遵义20余年的考古调查认定:“水东临清”城建于汉屯氏别河故道之东,即今临西县仓上村之东北,与“月洼寺”隔河相望近千米处之,“卧牛坑”。据传,古时曾有金牛卧此,固此成坑,故名。据当地老农讲,民国早年,卧牛坑一带依然是残砖破瓦,沙碱地,不种庄稼,长满茎柳,一片凄凉景象。他们在这里取土,尚见建筑基础之痕迹。野外调查表明,“卧牛坑”有200多亩大的面积,现已全部改造成了良田。但1963年洪水时,“卧牛坑”淤积达一米多河,故使古临清城深埋于地下。但从取土坑的断层发现,其淤积层下文化层包含物丰富,从标本采集到西汉的水井,陶瓷器残污。其下限是五代和北宋早年的磁窑瓷片。此由可判定,此遗址是五代和北宋之交时才废弃之。
古临清县城历史悠久、遗存丰富,是研究大运河文化的“活化石”。2006年5月30日,联合国地名专家根据联合国相关决议评审鉴定,认定临清为“中国地名文化遗产——千年古县”,并颁发认定证书。2013年5月3日“水西临清”古县城遗址也被国家文化部批准为国家级重点文化保护单位。如今,临清古城遗址(今临西县仓上)已成为大运河一个标志性文化符号。
在明清时期修建的北京故宫三大殿和南京中华门城以及曲阜的孔庙等地游览观光时,总爱立在墙下,各地墙体虽然不一,并已经好几百年了,久经风雨浸淋,但仍不碱不蚀,敲击有声,坚固结实,我为之暗喜,这些砖石都是我老家陈窑烧的,大运河“漕运”来的。
陈窑烧砖业远近闻名。始于明代嘉靖年间,陈、李两姓人家利用本地莲花土烧制的1米见方的方砖,质量上乘,体积之大,实属罕见,再加大运河“漕运”便利,这一带窑业受到皇室喜爱,立为官窑。每年向京城进贡御砖,用于修建宫殿等皇家建筑。北京除故宫三大殿外,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各城门楼、钟鼓楼、文庙;国子监及各王府营建都是用临清贡砖。并且明清三大陵等皇家陵园的“寿功砖”以及德州减水坝,张镇荆门、阿城、七级闸坝等处也相继用上临清贡砖。进而促使陈窑大扩张,有了皇窑、张窑、小白窑等“72窑”。形成了规模,成为当地一大主要产业。不久前,邢台市文物局对此勘探,现存的明清旧窑址仍有20余座之多。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今年深秋的一日,我返回老家临西。再次光顾经过冬天白雪的皑皑装扮,春意盎然的百花孕育、多情盛夏炙热滋养的大运河,更加浓墨重彩、迷人多姿、神韵悠然、气度不凡。但由于天气渐冷,游人稀少,顿时又觉此刻的运河寂寥了不少,空旷的河面上略显得苍凉凄清,大运河从春秋吴国伐齐开凿,隋炀帝大幅扩修,到今天的南水北调,已在历史长河中奔腾二千余年,它历经朝代更换的沧桑磨难,看过了太多的人世繁华,静静的储藏无数个春秋故事。古老的运河水变得有些干涸,浪花也没有当年的波涛翻滚,两岸的树叶变黄了,纷飞飘零,但一望无际的视野令我心中开阔不少,透露着一种雄浑、悲壮、诗意之美!我独自徘徊在堤坝上,任思绪尽情驰畅想,静坐在河边,望着涛涛的河水向前流淌,心中却想起历史的洪流和流传在这里的纷飞往事。远眺眼前景色,田野中玉米敞开外衣露出金黄金黄的躯体供人观赏,堤坝两岸上的红薯蔓藤正在拼命生长,河中的鱼儿时时腾空飞跃……,这运河金秋美景极尽眼底,风吹云动天不动,水推岸移船不移,划动的扁舟已留下河上一丝一缕的涟漪,荡碎了如镜的河面,秋风拂面,诗意无穷如梦似幻,深醉不已。
我的祖祖辈辈生长在我们祖先用血肉之躯开凿的大运河身旁,喝着它的甘泉,浸润着它的文化,领略着它的风情,吸收着它的氤氲灵气,是多么的幸福和自豪!而运河又像一道天然屏障,把临西县与临清市“一分为二”,两座一衣带水的姊妹城,如“牛郎织女”隔河相望。于是,勤劳智慧的两岸人设置了许多渡口码头,方便了两岸之间的往来。在我的记忆中,仅临西河段一侧就有大大小小的渡口10多个。我沿河寻找古渡旧址,不少上了年纪的人对此仍记忆犹新。在大运河与会通河交叉口处的登瀛楼,我有幸欣赏到室内珍藏的清代著名书法家王毅书写的“沙邱古渡”的匾额石刻。从这苍劲洒脱的字迹上,依稀感受到多年运河津渡的繁荣与悠然。
沿着运河岸寻访,那艄公雄壮的号子声,一阵阵在耳畔回荡,清风徐来,波光粼粼,川流不息,来来往往的船只拍打出的浪埂子像脊瓦般缱倦着漂浮,不时地打向岸边,当你踏上船头的那一刻,随着双棹划出的一个个酒窝,心就像云儿一样飞翔。你会感到整个世界都柔情似水,年华似水,整个人都柔情于水中。你会浮想联翩,这既不是白居易“浔阳江水夜送客”之地,也不是李白“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之处,从你这里扬帆启程的游子,既承载着厚重的齐鲁文化,又承担着鲜明的运河文化,又载着冀南红色文化,憧憬着美好的希望而去,满载着收获而归。
运河的水质是浑浊的,而只有浑浊,才能体现它的真实。运河一路行走的时候,它早已风尘仆仆,这些浑浊正是它卷起千里风沙的痕迹,它承载着与这个城市同岁的记忆,积淀下来的数千年历史风雨,交织成水乡临西人古朴淳厚的民俗民风,却依然在悠悠河水声中向人们倾诉……。
大运河走过了临西,在这里留下了脚印。作为“运河城”的临西,在今天,继续着新的发展,创造着新的历史。据我知,届届临西县委、县政府带领全县人民艰苦奋斗,改革创新,使古老的临西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临西的大街小巷都有着一种穿越了时空的韵味,都是对大运河文化神韵的强调,特别是新城的建设,两园一湖,幽静高雅,光明之光耀城东,朗朗书声发城西,处处春风浩荡,时时民风纯朴。这里的人们和这片热土将更加光彩夺目,前程似锦。
王金锋,男,河北省临西县人,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管理学院人文科学研究员,曾任《光明日报》、《中国经济时报》特约记者,邢台市政府研究室主任。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河北日报》和新华社、《求是》杂志社等中央、省媒体上发表2000多篇稿件,并先后出版长篇报告文学《龟志》,《100名人惜时故事》等著作15本(500万字)。
 手机版
手机版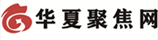 |
发现
|
发现

 京公网安备 1101150200481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1502004812号